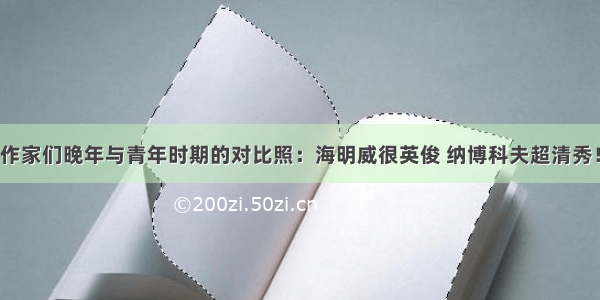林棹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9月15日,备受年轻读者关注的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公布。经过评委会成员苏童、孙甘露、西川、杨照、张亚东按照多数原则表决,进入决选名单的五部作品如下:林棹《流溪》、任晓雯《浮生二十一章》、沈大成《小行星掉在下午》、双雪涛《猎人》、徐则臣《北京西郊故事集》。
徐则臣是国内中青年文学实力中坚派代表,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双雪涛是近些年崛起的80后作家,写东北当代生活的代表人物,被称赞为“迟来的大师”。任晓雯和沈大成都是近几年作品频出的70后实力作家。其中任晓雯还曾获得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短篇小说奖”提名奖。相比而言,林棹这个名字在文坛显得比较陌生。林棹是谁?《流溪》写了什么?有怎样的特色?为什么能一鸣惊人?自然也引发一些读者的好奇。
《流溪》是林棹创作并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首发于《收获》杂志夏季长篇专号,4月小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如果按照阅读小说的常规方法,试图厘清她到底讲了什么故事,那么大概可以这么总结:小说以女主人公张枣儿的叙述展开,回望了童年、少年生活,以暴虐的父亲和绝望的母亲为代表的家族群像,和与浪荡情人杨白马的失意恋情。
但厘清情节、辨认人物,不是阅读这部作品的好方法。作为一部字数十万出头的作品,《流溪》最大特点是,文本的节奏、质感,很独特。纳博科夫式的倾述和描述,带来了强烈的陌生感和挑战感。迷雾般的语言,宝石般的幻象与狂想,引领我们仿佛走进一个历史和当下,回忆与当下,梦幻与现实交织的思想丛林。这部处女作充满难以描摹的幻象、狂想,天马行空的修辞,丰富的细节,多义的词汇与符号,将读者带进前所未有的意识漩涡,每一次重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发现。
“我叫张枣儿,一九八三年生于咸水城。和我同年出生的有菲利普·拉姆、艾米·怀恩豪斯、爱德华·斯诺登、苍井空。我爷爷张宝田参加过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两广追击战和解放海南岛……我奶奶陈坚、姥姥李晖都曾是揭阳地区进步少女,土改时期做过妇女干部……”中国第一家麦当劳、世纪初的互联网、盗版碟片、高速公路的速生林带、城中村、粤语、亚热带永夏的丘陵、驯化的植被……普遍的当代生活与南国独特的风物被作者以迷人的当代汉语重新搭建,戏仿、拼贴、反讽、引用……狂欢式叙事将现实冲散、重塑。这部处女作呈现细密画质地,携带着亚热带岭南独有的滋味、风景与记忆,讲述成长的歧途和可能的代价,纪念那些被随意折断与腐败在地的微弱者,和他们有过的爱与生活。
这部作品受到诗人翟永明和作家棉棉的好评推荐。棉棉说:“我觉得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阅读文学作品,一种人不阅读文学作品。林棹的小说值得推荐给阅读文学作品的年轻人。读者不必被她的语言狂欢的迷雾所困扰,《流溪》的写作就像是作者的一场又一场的内观,作者邀请我们进入她内在的丛林,她的写作呈现了诸多层面的现实——用的是迷人的当代汉语,尽管语言一次又一次害了我们。关闭手机一天阅读林棹,文学终究能够帮助我们整理我们的存在,愿所有的痛苦与伤心都能成为女孩子们佩戴的宝石。”
林棹1984年5月出生在广东深圳。,当时21岁的她就完成了《流溪》初稿。但稿件一度丢失。找到后,林棹改写,完稿。跟很多有写作理想但容易被现实生活带离她从事文学的年轻人轨迹相似,不写作的林棹也从事过跟写作完全无关的工作,比如实境游戏设计,卖过花,种过树。
,因为一场大病,让她决心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重拾文学写作,最终完成了《流溪》。9月,在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公布后,封面新闻记者联系到林棹,与她进行了一番对话。
专访林棹
《流溪》“是21岁的我和34岁的我合力完成的”
封面新闻:这部作品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入选“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有怎样的感受?
林棹:高兴。第一反应是我的编辑也许可以松一口气了。正因为它是我的第一本书,编辑需要承担更多,非常不容易。
封面新闻:《流溪》跟我读过的很多小说不都一样:它没有常规的叙事,形式上很先锋。遣词造句带有诗意的轻飘。事实上,它吸引我的也正是这意象斑驳的语感,天马行空的行文。一般来说,写作者的写作都是受其阅读的内容影响或者启发的。你是受到哪位作家的启发或者影响比较大?在我个人看来,这其中一定有纳博科夫?
林棹:知道纳博科夫是在前后,文学论坛里,他和好几位作家一起,被小范围地喜爱、分享。他的长篇文本,因为密度大、细节精美,往往在三读之后才彻底绽放。字里行间,你眼见他玩得精妙、投入、高兴。那是一种极具感染力和魅力的示范:如果文字是小说的唯一材料,它可以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它可以为作者和读者带去什么程度的欣喜;当然它同时带来一些问题——对纳博科夫主义者来说则不是问题——诸如,审美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吗?等等。
在纳博科夫之前我读过许多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就像某种青春期大门,纳博科夫则是一座轰然降落的宝石山,太异质了,以至于,对形式上的“惊奇”和“陌生感”的追求从此变成一种阅读上的偏执。这种偏执可能让我错失了一些东西。
封面新闻:能谈谈这部小说,作为写作者你寄托给这部小说的是要表达什么?完成它中,经历过怎样的过程?
林棹:《流溪》的前后两稿,是21岁的我和34岁的我合力完成的。当中的十三年,它以未能确定的形式躺在未能确定之处。现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比喻了,因为它被写完、拥有了确定的结局。它可以是关于成长的比喻,关于时间的比喻,关于际遇的比喻,诸如此类。而在被写完之前,它只是一个洞,被记着或被忘记。
21岁的我缺乏认知、经验、勇气,但不要紧,因为每个人在每个年龄段总会缺点儿什么;34岁的我拥有了这些,外加一点运气,于是很幸运地,可以动手把那个洞填起来。对我来说,洞变成了桥。有时,写作者和作品之间是互相救济的关系。
至于“小说要表达什么”,我倒觉得不必急于概括——小说恰好是反概括的,它是细节、细节和细节,具体、具体和具体。它是亲历。
“我记得成都冬春季的清晨时常起雾”
封面新闻: 这部作品里,应该有一些真实的生活或者人物影子。其中真实和虚构,是怎样的关系?
林棹:现实世界的非虚构性日渐松动,虚构世界则勉力虚构真实,两者共通的迷人之处在于,“真实”以神秘、不可测算的尺度扭转、变形,这一“不可测算”对作者和读者而言都成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每个角色都是我。“我”、爸爸妈妈、那排玉兰树、牛奶、失去牛奶的牛奶杯,都是我。于是我打我,我亲吻我,我冲着我喋喋不休,一群我走在放学路上。而小说中提及的城市,比如成都,变形作“浓雾城”——我记得成都冬春季的清晨时常起雾,伴随一种湿的低温,建筑物头颈胸消失,世界软化成乳白的流体——惟有主观的真实留存。
封面新闻:我看到报道说,“她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初稿,稿件一度丢失。被找到后,林棹改写,完稿。其间的里,她从事着跟写作完全无关的工作,种树、卖花,做游戏设计。”但最终你完成了这部小说。这中间遇到哪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在没有进行文学写作的里,内心有对写作的渴望吗?
林棹:20岁的时候,我对世界、对生活一无所知,但生活早就开始了,那个生活是先于你存在的、等待你去延续或打破的盒子。在我的盒子里,人们会认为想要写小说为生是疯了,毕业、拿工资、退休的路径才是正常、可靠。这是很普遍的观念。我一度接受了它,因为我二十几岁,对世界和生活一无所知,性格谨慎保守。勇气、决心、行动力一项都不具备。类似于,写作是一份礼物,我极端渴慕,却相信自己绝不可能得到,于是不仅放弃了,还躲得远远的,因为看到、想起都会伤心。重新写作之前一直是这个心态。就是过活,干点别的,过活。
封面新闻:后来是怎么又重拾文学写作的?
林棹:底,无端地开始做一点小练笔。觉得特别带劲。就是高兴。还没来得及做什么长远计划,初旅行时撞上流感,病毒性心肌炎,几乎死掉,但是活了过来。重新睁眼,病房很白,身体很轻,我猜重装系统之后的电脑和我会有同感。我觉得那就是运气:重病和病愈,来得又快又急,一场极度逼真的死亡模拟。经历过的人,恐怕都会重新打量生活,掂量清楚什么才是真正快乐和值得过的人生。那年我34岁,那场病帮我做了全职写小说的决定——一方面身体需要静养康复,静养期至少一年;另一方面家属全力支持。
封面新闻:给这部作品起名“流溪”,是怎样的想法?
林棹:相比自上而下的、大的、外向或关注群体的探索,《流溪》是关注个体的、内向的、近距离的,溪水的意象符合这些特征。个体的声音深埋在群山密林之中,需要凝神倾听,同时那些倾诉也如溪水一样万变、充满不确定性。
封面新闻: 你现在是专职写作?下一部作品是怎样的进展?平时不写作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林棹:第二个长篇已经完稿,从19世纪初的广州出发,循着江河、海洋扩展,文字上做了方言写作的试探。对我来说它是很有意义的一段旅程,把我送至充满惊奇和陌生感的天地,其中的一切静待唤醒。目前在为第三个长篇做准备工作,包括阅读、踩点、写法上的摸索。有时出门观鸟,迁徙季出门更频繁些。